
这些参加“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的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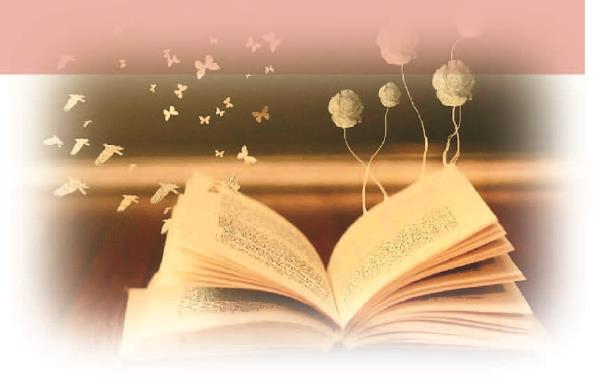

扫码看视频
◆ 华心怡
“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之后,共收到近5000封海内外来稿,其中20篇经评选成为“夜光杯美文”,将于9月9日晚在新民晚报创刊95周年系列活动“夜光杯之夜”上揭晓。
用小文章表现“新时代”,用好文字唱出“新旋律”,寻常如你我,也可以与大师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夜光杯”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因文字而闪光——这里是一些参与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的素人作者的故事。走近他们,走进“夜光杯”朋友圈。
1 戚舟 阿勒泰有棵树
戚舟的家乡是阿勒泰。连续剧《我的阿勒泰》火了,无数城里的人们向往广袤的草原上,白云底下的马儿跑的一幕幕。甚至,连她们面颊上红红的两团,都那么质朴,那么可爱。但对于戚舟来说,她的阿勒泰显然不是镜头里的种种。“电视里大概拍出了60%吧。”戚舟一家都是从河南移居至当地,家里的老一辈到现在说的都是河南话。不似我们想的,30岁出头的戚舟大概只见过草原一两次,对她来说,那也是稀奇。
戚舟去喀什支教了两年。入村的那条路十八公里,她来来回回,报废了一辆电动车。那里,二十六个宝贝等着她。戚舟教宝贝汉语,以及如何种下梦想。都是宝贝,但宝贝和宝贝还是不同的。戚舟喜欢“布布”,一个六岁的女孩,有着一双黑葡萄般的眼睛。布布是戚舟唤她的,软软糯糯像小布丁。布布是班级里个头最小的。她的爸爸是警察,哥哥也曾是警察,后来执行公务时牺牲了。布布说她也想当警察,大家都笑,这么小小的、软软的身子,能抓得住谁呢?戚舟却没有笑,她告诉大家,把一个梦埋进土里,用勤奋和智慧去浇灌,有一天,就可以发芽、繁茂,变成理直气壮。
戚舟工作在兵团上,这些年,她开始写作投稿。在小红书上看到了夜光杯的征文活动,她说自己不能错过,毕竟,戚舟看新民晚报已经好几年了。“每次攒上两三个星期,然后一次看完电子版。”戚舟的梦想,也是自己的小学老师为她种下的。小学一年级,她就遇上了白老师。白老师也年轻,她喜欢戚舟。每次小小的女孩考试考得不错,她就自费买一本书送给女孩。到现在,戚舟都记得自己收到的第一本书是《绿野仙踪》,故事中充满友情、忠诚、诺言、合作,当然还有一路上的成长。到了三年级,学校里终于有了图书室。她曾觉得很大很震撼,一墙壁一墙壁的书,但现在想想也不过是一间屋子的大小。正是因为不大,并不对每个学生开放。又是白老师带着戚舟办好了图书证。后来她当过小记者,采访学校的运动会、音乐会。再后来,白老师走了,但戚舟读下的那些书,看过的那些字,却一直留了下来。
戚舟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美国作家贝蒂·史密斯写的《布鲁克林有棵树》。贫民区布鲁克林的小女孩弗兰西,饱经家庭的不幸,同学的歧视和社会的不公。但她艰难地成长,从未放弃写作梦,她每周总要央求图书管理员为自己推荐一本书,这是让她走下去的一点光。“你看一切,要像第一次或最后一次见到的那样,如果这样的话,你在世上的日子就会充满荣光。”布鲁克林的那棵树是天堂树,这种树是唯一能在水泥地里长出来的树。对于戚舟来说,阿勒泰也有棵树,向阳、向上、充满爱。
2 亚历山大 我为申花狂
亚历山大的标志是丸子头。他有点名气,名气在申花朋友圈。一个美国人,“扎”在上海10年,大概没有什么比成为一名“蓝魔”能更直接、更深刻地融入这座城市了。无论是抖音,还是B站,这个跟着申花一起笑一起哭的老外,成为阿拉的自己人。
亚历山大出生在佛罗里达,那里有大海,那里有热力,人人似火。但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是内敛的,他说一直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外放张扬的性子。去到大学,学了数学、社会学,还学了一点中文。大学,是个崭新的物理空间,各种社团,各种实践,亚历山大被整个“打开”。原来,他并不是自己以为的自己。人,有意思极了。他会等待某个时间节点,或某次化学反应,自我“爆破”,一步步走向更真实的内心。亚历山大问自己:你真的想呆在学校里研究数学,日复一日地做研究吗?亚历山大给出的答案是:他来到了中国。
南通是亚历山大的第一站,他做外贸。人的一辈子,或许都在寻找童年。自小,去体育场看各种比赛是家里的保留节目。棒球、橄榄球、足球、NBA……倒不一定真的是谁的死忠,“燃烧”的现场气氛,还有那种“在一起”的家庭记忆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来到中国的亚历山大急切地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赛场归属。遗憾的是,那几年,南通并没有中超球队。转场上海,开启自己的第二段中国旅程,他迫不及待地走进体育场。但申花还是海港呢?这是个问题。
亚历山大打算去两边的主场都观摩下,然后给自己定下一个主队。第一站,是申花。那时的申花还在虹口。一下子,亚历山大就被“吸”进去了。球迷灼热的情感,现场燃爆的气氛。亚历山大只看了一场,便坚定:就是申花了。后来,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选择,一起享受,一起欢呼,申花球迷的忠诚度和积极度,是有魔性的。亚历山大的办公桌上,放着申花的搪瓷杯,手机壳,也是申花限定款。
亚历山大已不满足主场观战了,他成为申花球迷中的“远征军”。有时候,太太会抱怨他为了看申花比赛,花钱花得太多,花时间花得太多。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已与上海合二为一,因为他成为了“蓝魔”的一员。“蓝魔”是有门槛的。早前,他看到有“蓝魔”国际团的球迷,主动上前搭讪。亚历山大说,别人是用“斜眼”看自己的,只以为又来了一个看看玩玩的老外。结果,一场又一场比赛,一次又一次遇见,这个老外居然回回都来。国际团的球迷主动向亚历山大伸出橄榄枝:比赛前一起吃个饭吧,看球时一起来北看台吧……亚历山大被接受了。
他说自己不是那种荣辱不惊的球迷。申花赢了球,他要高兴好几天;输了球,便也要低落好几天。和亚历山大聊天,正是他去客场观战申花本赛季联赛首败之后的第三天,他不太开心,“还没有走出来”。做申花球迷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是,一直和大家“混”在一起,亚历山大的上海闲话也越来越好了——讲不来,听得懂。这一次,在社交媒体上有点红的亚历山大决定到晚报上用汉字写写自己与申花的故事,写写自己作为上海人的故事。
3 高慧凝 文字会跳舞
高慧凝正在攒字,她为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做准备。说起来,她的这条职业路线并不是始终明晰的,倒像是一张画了很多箭头的地图,尝试了好几个方向,终于找到自己的目的地。高慧凝当过一年的幼儿园教师,便“撤”了。她说,不那么合适。后来,她又去做了舞蹈培训,甚至还想过开一间自己的工作室,终也未果。文学,突然冒了头,给了女孩一份生活的灼热感,让她想要去试试。高慧凝不是拖泥带水的,她立即去考同济大学创意写作班。两年,沉了下去,沉入文学与写作,再起身,便已坚定——原来所有的兜兜转转,都是为了找到此处。
有时,高慧凝会拿自己的小作品给一些前辈看。前辈有指教:小高啊,好文章需要有时代性的见解。但小高有自己的观点:“我不能保证自己的文章有卓越的见识,或者给读者带来信息的增量,但我可以保证的是,这些文字都是我当下的有感,都是真实的。真实性并不指文章内容的真实,而是我个人情感的真实。只要我的作品能引起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就达到了我的初衷。”情感的真实,这不也是高慧凝对待生活的态度吗?
跳舞是童子功,三四岁的时候就练上了,长大后还去了上戏附属的舞蹈学校。跳舞是苦的。身体上的苦,咬咬牙也就过来了。更苦的,是心灵上的焦灼。“跳舞时候会有选拔,这份竞争感不亚于学生读书考学。”现今,她想了想,跳舞和写作有什么相通或不同呢?不同处很明显,一动一静。“相通的地方也有,它们都是通过外在的形式,写作借助文字,舞蹈通过肢体,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读者和观众都可以有自己的二次解读。这便是千人千见。”她依旧喜欢舞蹈,看得很杂。芭蕾、古典舞、拉丁舞、现代舞,城中有舞蹈演出,她大多都不会错过。近期让高慧凝印象深刻的,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文字也会跳舞,流淌着流淌着,高凝慧说是自由自在的感觉,然后汇聚成一条情感的河流,让人沉浮其中。
4 童中平 黑暗里的光
童中平59岁了,来自江西萍乡。他每天都会听书。什么都听,小说、杂文……他喜欢励志的、向上的内容,这些句子,像他生命里的光。大概没有人能够理解,文字对于童中平的意义。因为,我们的世界是光明的,透亮的。
10岁那年,童中平看不见了,世界从五彩斑斓变成了漆黑一片。他受了外伤,头部撞上硬物导致视网膜脱落。这是一记来自命运的重锤。那时年少,倒也未觉太多煎熬。难受的是,他不能看书了。书本里那么多的志怪、英雄,那么多的冒险、探索,统统离他远去了。后来,童中平抽脱自己,来审视遇到灾祸时那个小小的孩童:“比起其他的不方便,这才是男孩最痛苦的地方。”其实,半个世纪前,世界的多彩,很多都是书本铺设的。
20岁出头,童中平才学了盲文,又去了学校学习按摩。一毕业,童中平进了医院的按摩室工作。他开始慢慢找回自己的轨道,第一就是要重新阅读。那时,盲文书很少,看得也很慢。他慢慢试着写作,用盲文写出来,再找人抄成汉字。有了点名气,甚至还出过两本小书。“年轻的时候是有过文学梦的,但后来我发现真正的梦想,倒并不一定是要功成名就,成为什么大作家。其实一辈子读书,读很多书,就是一个梦了。”
童中平是实实在在看到时代变迁的。残联给他发了一个听书机,外头买也要六七百元。这是他的“宝贝”,每天捧在手里。现在,童中平用上了微信。“有很多读屏App什么的,沟通没有障碍。”这次的夜光杯征文,他就是从微信群里“听”来的。甚至写文章,也变得方便起来。一个人,一台机器,一个软件,统统搞定。童中平如今也爱听一些游记,字里行间的风土人情,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仿佛他自己也走了一遭。
文学,是黑暗里的一道光,童中平说:“每天,不看点书,不写点东西,就浑身难受。它们已经像吃饭一样,成为生活中的必须。”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